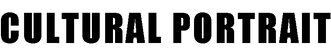Z 世代面臨的前所未有的行為健康挑戰
內 容 分 類 :
麥肯錫進行的一系列消費者調查和訪談發現,Z 一代報告的生活前景最不樂觀,包括比老一代人的情感和社會福祉水平更低。
在美國爆發 COVID-19 大流行近兩年後,從中學生到早期專業人士的 Z 世代報告的焦慮、抑鬱和痛苦發生率高於任何其他年齡組。這一代人的心理健康挑戰如此令人擔憂,以至於美國外科醫生 Vivek Murthy 於 2021 年 12 月 7 日發布了一項公共衛生諮詢,以解決因 COVID-19 大流行而加劇的“青年心理健康危機”。
麥肯錫進行的一系列消費者調查和訪談表明,各代人之間存在明顯差異,Z 世代報告的生活前景最不樂觀,包括比老一代人的情感和社會福祉水平更低。四分之一的 Z 世代受訪者表示情緒更加痛苦(25%),幾乎是千禧一代和 X 世代受訪者報告水平的兩倍(各 13%),是嬰兒潮一代受訪者報告水平的三倍多(8%)。而 COVID-19 大流行只是放大了這一挑戰(見邊欄,“COVID-19 大流行的不成比例的影響”)。雖然消費者調查當然是主觀的,而且 Z 世代並不是唯一經歷痛苦的一代,但雇主、教育工作者和公共衛生領導人在規劃未來時可能希望考慮這一新興一代的情緒。
在我們的樣本中,Z 世代受訪者比 X 世代或嬰兒潮一代更有可能報告被診斷出患有行為健康狀況(例如,精神或物質使用障礙)。 在 2019 年末至 2020 年末的 12 個月期間,Z 世代受訪者表示考慮、計劃或企圖自殺的可能性也是其他世代的兩到三倍。
Z 世代還報告了比其他任何一代人更多未滿足的社會需求。 58% 的 Z 世代報告有兩個或更多未滿足的社會需求,而老一代的這一比例為 16%。這些感知到的未滿足的社會需求,包括收入、就業、教育、食品、住房、交通、社會支持和安全,與更高的行為健康狀況自我報告率相關。正如最近的一項全國性調查所示,心理健康狀況不佳的人報告基本需求未滿足的可能性是心理健康狀況良好的人的兩倍,而基本需求未滿足三個或更多的可能性是四倍。
隨著這些年輕人努力發展他們的複原力,Z 世代可能會尋求他們所期望的整體健康方法,包括身體健康、行為健康和社會需求,作為未來的學生、員工和客戶。
醫療保健生態系統中 Z 世代消費者的特徵
Z 世代的特定需求表明,改善他們的行為保健將需要利益相關者增加訪問並提供適當、及時的服務。
Z世代不太可能尋求幫助
與其他世代相比,Z 世代受訪者更有可能報告有行為健康診斷,但不太可能報告尋求治療。例如,Z 世代報告不因行為健康問題尋求治療的可能性是千禧一代的 1.6 到 1.8 倍。有幾個因素可能導致 Z 世代缺乏尋求幫助:發育階段、脫離醫療保健、感知負擔能力以及與家庭和社區中的精神或物質使用障礙相關的污名。
Z 世代受訪者認為他們的醫療保健參與度低於其他受訪者。約三分之二的 Z 世代受訪者屬於醫療保健消費者參與度較低的細分市場,而其他幾代受訪者的這一比例為二分之一。Z 世代和這些參與度較低的人群中的其他人報告說,他們對自己的健康和壽命的控制力較差,對健康的意識較弱,對保持健康的積極性也較低。三分之一的 Z 世代受訪者屬於參與度最低的部分,他們報告說改善健康的動機最低,並且最不喜歡與醫生談論行為健康挑戰。
Z世代減少尋求幫助的另一個驅動因素可能是心理健康服務的可負擔性。四分之一的 Z 世代受訪者表示,他們負擔不起心理健康服務,在所有接受調查的服務中,心理健康服務的可負擔性最低。 總體而言,患有精神和物質使用障礙的美國人承擔了不成比例的自付費用醫療保健費用,原因有很多,包括許多行為健康提供者不接受保險的事實。“我找到了最適合我的治療師,但我買不起她,即使有保險,”一位 Z 世代受訪者說。“獲得心理健康治療的最大障礙是經濟上的,”另一位補充說。
此外,與精神和物質使用障礙相關的污名以及缺乏家庭支持可能是尋求精神保健的重大障礙。許多 Z 世代依賴父母提供交通或健康保險,並且可能害怕與父母就心理健康話題進行互動。這個因素與有色人種社區特別相關,他們報告認為與行為健康狀況相關的污名程度更高。 移民的孩子也可能因為父母的犧牲而內化內疚,或者他們的父母可能將行為健康問題最小化,他們可能會說或認為他們的孩子比他們長大“更容易”。
Z世代在尋求幫助時依賴緊急護理、社交媒體和數字工具
當他們確實為行為健康問題尋求支持時,Z 世代可能不會求助於常規的門診心理健康服務,而是可能依賴緊急護理、社交媒體和數字工具。
Z 世代比老一代更頻繁地依賴緊急護理場所,Z 世代受訪者報告使用 ER 的可能性高出 1 到 4 倍,報告使用危機服務或行為健康緊急護理的可能性高 2 到 3 倍過去 12 個月。Z 世代還佔 Crisis Text Line 用戶的近四分之三。 一位 Z 世代的受訪者表達了她的沮喪,她說:“似乎唯一的選擇是去急診室就診,否則我必須等待數週才能去看精神科醫生。”
幾乎四分之一的 Z 世代還報告說,在行為健康危機期間獲得幫助“非常”或“非常”具有挑戰性。在過去的 12 個月中,這一代人因自殺意念或企圖自殺而尋求治療的可能性是其他任何一代人的兩到三倍。
許多 Z 世代還表示,他們應對行為健康挑戰的第一步是去 TikTok 或 Reddit 尋求其他年輕人的建議,在 Instagram 上關注治療師,或下載相關應用程序。這種對社交媒體的依賴可能部分歸因於該國許多地區的提供者短缺:美國 64% 的縣缺乏心理健康提供者。此外,美國 56% 的縣沒有精神科醫生(相當於總人口的 9%),73% 的縣沒有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科醫生(相當於總人口的 19%)。
Z 世代對他們接受的行為健康服務不太滿意
Z 世代表示,行為醫療保健系統總體上沒有達到他們的預期——接受行為醫療保健的 Z 世代與其他世代相比,不太可能報告對他們所獲得的服務感到滿意。例如,與老一代相比,Z 一代報告對通過門診諮詢/治療獲得的行為健康服務的滿意度較低(Z 一代為 3.7,而 X 一代為 4.1)或強化門診(Z 一代為 3.1,相比之下老一代為 3.8)。 一位 Z 世代受訪者表示,“努力尋找一位讓我感到舒服並足夠關心以記住我的名字以及我們前一周所做的事情的心理學家”是最大的護理障礙。另一位說:“我有信任問題,很難與治療師談論我的問題。我和治療師的經歷也很糟糕,這讓這個問題變得更糟。”
儘管我們看到遠程醫療在精神病學中的普及率很高(2021 年 2 月遠程醫療門診和辦公室就診索賠的份額為 50%),Z 世代對遠程行為健康的滿意度最低(Z 世代對遠程醫療的滿意度為 3.8,滿分 5.0,而老一代的滿意度為 4.1)和數字應用程序/工具(Z 世代的滿意度為 3.5,滿分 5.0,與老一代的 4.0 相比)。圍繞遠程醫療,Z 世代提出了不滿意的原因,例如遠程醫療治療感覺“不那麼正式”或“不那麼專業”,以及更難與治療師建立信任聯繫。對於應用程序,Z 世代受訪者指出缺乏個性化和多樣性——無論是在他們呈現的故事的種族和民族多樣性方面,還是在應用程序提供工具解決的問題方面。在創建和改進行為健康工具時,採用以用戶為中心的設計方法來開發 Z 世代真正想要的功能和體驗至關重要。
Z世代在選擇醫療保健提供者時關心多樣性
行為健康勞動力的種族和民族多樣性也很重要。根據麥肯錫的 COVID-19 消費者調查,少數族裔和少數族裔受訪者報告稱,他們在選擇醫生時重視種族和民族多樣性,他們比白人受訪者更頻繁地引用他們醫生的種族作為考慮因素。
由於 Z 世代非常關心多樣性,因此有機會通過提供更具種族和民族多樣性的行為健康勞動力和文化相關的數字工具來整合護理和早期干預。
滿足 Z 世代需求的潛在利益相關者行動
在我們的文章“通過行為健康解鎖全人護理”中,我們概述了六項潛在行動,這些行動對於提高數百萬人的行為健康狀況的護理質量和體驗不可或缺。其中許多槓桿適用於 Z 世代,但需要進一步調整以最好地滿足這一新興一代的需求。有希望探索的領域可能包括數字和遠程醫療的新興作用;需要以社區為基礎對行為健康危機作出更強有力的反應;更好地滿足 Z 世代生活、工作和上學的需求;促進心理健康素養;投資於與身體健康同等的行為健康;並支持一種涵蓋健康的行為、身體和社會方面的整體方法。
現在需要採取行動
Z 世代是我們的下一代領導人、活動家和政治家;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承擔了成年人的責任,因為他們開始了氣候運動,領導社會正義遊行,並推動公司更緊密地與他們的價值觀保持一致。醫療保健領導者、教育工作者和雇主都可以在支持 Z 世代的行為健康方面發揮作用。通過採用量身定制的代際方法來設計信息、產品和服務,利益相關者可以有意義地改善 Z 世代的行為健康並幫助他們充分發揮潛力。這項投資可以被視為我們未來的首期付款,將在未來幾年產生社會和經濟回報。
關於作者
Erica Coe是麥肯錫亞特蘭大辦事處的合夥人,共同領導醫療保健社會福利中心, Jenny Cordina是底特律辦事處的合夥人,領導麥肯錫的消費者健康洞察研究, Kana Enomoto是華盛頓特區辦事處的高級專家和共同領導醫療保健社會福利中心, Raelyn Jacobson是西雅圖辦事處的合夥人, Sharon Mei是紐約辦事處的專家, Nikhil Seshan是費城辦事處的顧問。
作者要感謝 Tamara Baer、Eric Bochtler、Emma Dorn、Erin Harding、Brad Herbig、Jimmy Sarakatsannis 和 Boya Wang 對本文的貢獻。
訪問麥肯錫網站了解更多詳情
了解更多我們的 希 望 公 益